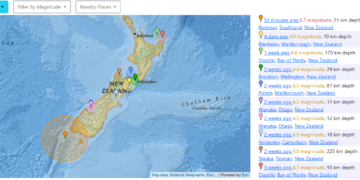图/视觉中国
文/邝海炎
本文首发于总第859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又到了毕业季,各大学的毕业寄语都在网上流传开来。厦门大学的邹振东教授2016年就因此红了一把,他今年的讲话稿《苟富贵,一定相忘》虽不如前年精彩,但也有看点。比如,说现在同窗四年“不杀”,就要感谢舍友大恩了。我们老家形容一个人易冲动就说他“气性大”,邹教授这段话也是对当前社会“气性大”的无奈自嘲。
可不是吗?想必大家都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,生怕自己哪天还不知道得罪谁就遭了殃。就说最近,6月28日,上海两儿童在校门口被杀害,警方说是凶手“报复社会”。6月29日,广州大学一院长因科研利益纠纷将该校科研处长夫妻捅死,然后自残。
这两起悲剧发生时,我刚好读完《诗经·葛屦》,写一个婢女辛劳缝衣却不受待见的心声。
开头是:“纠纠葛屦,可以履霜。掺掺女手,可以缝裳。”这是说,她脚上穿着破凉鞋,走在满地冰霜上,饿得双手如枯枝,还要给人缝制衣裳。
给谁缝制呢?给女主人。“要之襋之,好人服之。”
衣服做好了,还要提着衣领、扯着腰身,恭候女主人来试。女主人满意否?“好人提提”,她很满意。
可满意有什么用呢?“宛然左辟,佩其象揥。”人家压根不领情,看都不看我一眼,就左转身离去,还拿起簪子自顾梳妆打扮起来。“宛然”一词,生动地写出了那种把别人的劳动视为理所当然的神态。
所以,遇到这么小心眼大脾气的人,我只好写首诗讽刺一下:“唯是褊心,是以为刺。”
《葛屦》说明,“气性大”不只是一个人的性格问题,也与他(她)的生活遭遇有关。遭遇不平,便产生了“气”。怎么消“气”?有人逆来顺受惯了,根本就没有“气”。《葛屦》里这婢女倒有个性,有“气”,还采取写诗的办法撒了出来,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解决“气性大”的通用办法——“温柔敦厚,诗教也”,用文学之美来化解人身之“气”。
可当社会结构失范、规则不公、表达无渠道时,“诗教”也是枉然。在“史诗”小说《白鹿原》里,地主白嘉轩出钱让长工的儿子黑娃去上学,旁人看来这是好事,怎么黑娃这狗日的不领情,还怨恨上白嘉轩了呢?原来黑娃看不惯白老爷腰杆太直,以致多年后回来革命只用棍子打了他的腰。很多读者觉得这理由可笑,简直莫名其妙。莫名其妙就对了!这就活生生说明:革命并非都是出于经济理性人的选择,或者大而无当的“权利觉醒”,有时就是情绪推动,“一张脸一口气”而已。黑娃的心里话是:“我爸一辈子是你下人就算了,凭什么我一辈子也是你家下人!”白嘉轩确实算开明地主了,但在黑娃这种革命者看来,他们要打倒的不是白嘉轩这个自然人,而是“地主-长工”这种社会结构。“恨”有具体对象,“怨”却没有,“怨”针对整个社会结构,所以很多自认遵循社会规范、清白做人的“白嘉轩”们都莫名其妙遭殃了。
钱谦益曾描写明末的世态人心:“劫末之后,怨怼相寻。拈草树为刀兵,指骨肉为仇敌。虫以二口自啮,鸟以两首相残。”我们要规避这种状态,不能奢望每个人都受过“温柔敦厚”的诗教,而应从两方面发力。
一是制度改进。市场经济发展后,社会分工多样,今天你给我倒茶(酒店服务员),明天我给你泡脚(按摩师),谁都有为别人服务的时候,多样化可消解职业歧视,流动性可减少阶层固化。
二是尊重他人。当你在享受别的人服务时,要对从业者有起码的尊重,这样能减少阶层隔阂。如果乡下大妈背着孙子给你擦皮鞋,你对人家友善一点,可能她孙子的心中就不会埋下仇富的种子。
邹教授在毕业寄语中说:“一个最理想的社会,不是一人得道,鸡犬升天,而是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主体,承担自己的责任,挑战自己的命运,痛苦自己的痛苦,幸福自己的幸福。”这也是英国诗人约翰·多恩所说的,没有人是一座孤岛,可以自全。
作者系资深媒体人,著有《快刀文章可下酒》